以下文章来源于人文日新陈来 ,作者陈来
今年是杜维明先生八十寿辰,杜先生的友人、弟子、后学各撰论文,结为此集,为杜先生寿。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杜维明先生是驰誉海内外的著名儒学思想家,若从其大学时立下弘扬儒学的宏愿算起,他的儒学思考已愈六十年。纵观杜先生六十年来的学思历程,其思想经历了不同阶段,每阶段有其关怀的重点。而且,他在近三十年间,拓展了众多论域,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考。那么,在其学术思想的领域,有没有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以为,从“地方性知识”迈向“全球性意义”,乃是他学术生平中越来越清晰的思想要求,也是他推动诸多论域后面统之有宗的方法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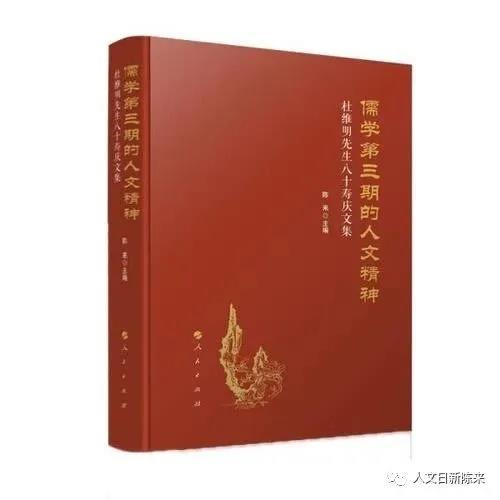
这一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历程,决不是从行迹上说的。虽然,杜先生从东海大学毕业,到哈佛大学求学,先后任教于美国顶级大学普林斯顿、伯克莱和哈佛,学术活动和思想对话的足迹遍及世界。而我们对其思想学术走向的把握,并非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而是指其儒学追求的文化自觉。杜维明先生青年时代在台湾便已明确确立了对儒学的认同,并开始置身于当代新儒家的阵营。而哈佛留学时期则是其儒学理想转型的起点。哈佛数年的留学使他超越了原有的仅仅从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儒学观,而转进至在希腊—希伯来为代表的轴心文明的视野中重建儒学人文精神的探索。于是,从1966年开始,从欧洲回归东亚的旅行,正式开启了他的儒学探索之旅:“儒家的话语如何在与两希文明的对话中获得新生命、找到新思路”。这也就是他后来常说的“绕道纽约、巴黎、东京才能回家”的思想内涵,即通过和世界各地体现轴心文明的大师大德交流、讨论、对话,找到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话语,这才是他心目中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然而,这决不是脱亚入欧的路径,而是在“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间,在“本土的根源性”和“全球的普世性”之间建立起辩证的有机联结。就地方性而言,他没有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反而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更为加深,并且提高了自觉。就全球性而言,他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这一观念的深刻理解,激励了他在扎根精神家园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创造性的对话,不断追索儒学的、当代的全球意义,从而使阐发儒学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日益成为他的自觉志业。

为了开展这些交流对话,他建立了多个论域,以为最终的凝道进行准备。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如“现代性”的反思,“宗教性”的理解,“精神性”的拓展等等,为他的理论的建立确立了基础。他主张现代性不能忽视传统,现代性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尤注重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他重视儒学的宗教性维度及其意义,认为宗教性有助于认识儒学的生命形态,超越启蒙的平面思维局限,与终极信仰相沟通。他以精神性来联系人与自然和天道,以对治启蒙的凡俗性人文主义。今天,在对他的思想进行总体把握时,我们需要超越那些众多论域的具体讨论,以把握住其背后的主导线索和归结,来解释他六十年来的哲学探索与建构方向。这就是,在他的英文学术写作和公共领域论说之外,在几十年来的儒学思考中,他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出这种自觉,即通过与世界各地各大精神传统及地方文化的对话,建立包含个人、社群、自然、天道四维的新体系,以表达新的人文精神,来体现儒学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他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最终凝结为一个特定的体系,他在其后期把这一体系命名为“精神性人文主义”。这一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学,不是对古典儒学的复制,也不是“当代新儒家”的简单延伸,而是以儒学为基础,对全球性地方知识的一种建构,这也是他的“做”儒家哲学的道路。换言之,他中年以来在“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指引下,广泛关注各种思想文化的论域,而在其后期,他把在这些论域中形成的思考,凝结为、归向于一个中心点:“精神性人文主义”。在其后期思想中,精神人文主义不再是一个准备性的论域,而是一个总结性的体系,他用这样一个体系来揭示儒家思想具有全球性的普世意义,或者说建构起具有全球性普适意义的当代儒学。

几年前,我曾经为他的论著集写了推荐辞,我把其中一段写在下面,与大家分享,作为本前言的结束:
杜维明先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他提出,新轴心时代的儒家已经从“一阳来复”走进了“否极泰来”,而当务之急是超越凡俗人文主义,重构新的儒家人文主义。这将使受启蒙心态和现代性所影响的凡俗人文主义,转变为充满生态关怀、有敬畏感和终极关怀、以儒学普世价值与现代性价值互动的新轴心时代的儒家人文主义,即“精神性人文主义”。杜维明先生的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且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具有重要、深刻的意义。
陈来
2019年8月5于北京
(本文是陈来教授为《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维明先生八十寿庆文集》所作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