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17年10期,
摘要
本文结合福柯的话语理论,讨论构建富有民族性特色的话语结构及其表达方式对于电影、特别是动漫电影的重要性。通过对比多部中美动漫电影中中国元素的运用方式,说明两者在本质上的趋同性,凸显拥有民族性话语的中国动漫电影所陷入的后殖民主义困境。面对困境,动漫电影构筑民族性话语有三条原则:首先,从既有的全球化话语语境(美国式抑或日本式话语结构)当中溢出,构筑具有例外性的故事情景;其次,从动漫故事架构当中应能透露出对于当下中国生存状态的反思和追问;最终,其故事的形象设定,应是建基于不同中国元素之融合而进行的一种新的创造。本文以对《大护法》中诸隐喻性内涵的分析来展现以上原则的现实化方式。
中国动漫电影自20世纪20年代始,发展至今几近百年。但其发展路径却并未能与中国电影的发展节奏同步,即它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而获得迅速成长。相反,一部完成于1964年的《大闹天宫》几乎成了中国动漫电影人的“龙门”,极尽努力却总是不可跨越。中国动漫电影的这一现状,大约源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在中国,由于缺乏一种成人动漫的文化传统,动漫电影缺乏明确的观众群体,从而使资本对其市场价值的预估缺乏信心,换言之,动漫电影拥有着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形态,其对内容与形式的深度内涵有所诉求,但其动漫的表达形式却同时将有能力理解其内涵的成人拒之门外。于是,近年来充斥着中国动漫电影屏幕的几乎是同名动画短片系列剧的衍生物,例如深受低龄群体欢迎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与《熊出没》等大电影系列。此类动漫电影的成功只能归结为动漫形象商业化运作的成功,它们不仅没有能够推动中国动漫电影的发展,反而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将中国动漫电影指引到一条“去电影化”的道路之上:将电影变成加长版动画系列剧的续集。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动漫电影总是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民族性话语结构及其表达方式,为数不多的拥有独立电影脚本的动漫电影仍然无法摆脱对美国模式抑或日本模式的东施效颦。近年来赚足口碑与票房的《大圣归来》(2015)、《大鱼海棠》(2016)以及刚刚上映的《豆福传》(2017)都可归入此类。相对于资本的匮乏而言,缺乏民族话语结构成为阻碍中国动漫电影发展更为严重的桎梏。本文将着力于探讨在中国建立这一话语结构的可能性路径,并以2017年上映的《大护法》为案例,展现这一可能性路径的实现方式。
1动漫电影与构建民族性话语的内在关联
谈论民族性话语结构及其表达方式,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话语理论的内涵。话语理论作为分析当代文化形态的有效工具,其根本在于话语本身内涵的实践性维度。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中的“语言学转向”。自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与其所指物剥离开来,从而构筑了一种富有独立性和能动性的能指与所指系统以来,话语理论就开始进入理论视野。在福柯之前,包括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海德格尔都或多或少对话语产生了兴趣,但福柯的话语理论显然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虽然福柯也没有给予话语理论确切的、始终如一的界定,但其丰富的内涵恰为这一概念注入了独特的理论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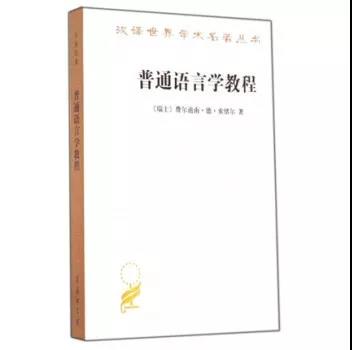

《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
“话语”,源于拉丁文的“discursus”,意为四处奔跑。由此演化而来的法语概念“discours”,也包含着自由闲谈、天马行空的内涵。它自身包含着一种实践性,在福柯及其后继者那里总是作为一个“动词”发挥着效用。福柯时常谈论话语的生产,这种话语生产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知识型,它们构成了人文科学展开自身的一种方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给予“话语”这样一种界定,即“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 (1) 。这一陈述整体,即作为动词的话语所构筑的是一个介于语言与言说主体之间的无主体性结构,后者具有去中心化的色彩,它成为了人们如此这般言说事物背后的隐性背景。伊格尔顿这样理解福柯的话语实践:“最有用的是把‘文学’视为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赋予某些种类作品的一个名称,这些作品处于被米歇尔·福柯称为‘话语实践’的整个领域;如果有什么确实应该称为研究对象的话,那就是这一整个实践领域,而不仅仅只是那些有时被迫模糊地标为‘文学’的东西。” (2) 这一对话语实践的运用是准确的。换言之,话语从未意味着一整套外在的语言,抑或这一语言的言说方式,而是在于支配这一语言及其言说方式的结构,而这一结构总是会被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所左右。因此,对话语结构的建立,并不是展现出其究竟有什么样的知识型的发展历程就完成了,而更多的意味着需要回答究竟什么样的历史情境能够产生如此这般的话语结构。在1970年福柯就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时候所发表的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所关注的是话语所承受的一定程序的选择、控制与筛选,从而将话语与权力的问题再一次紧密联系起来 (3) 。更进一步说,话语理论并非仅仅是客观的、表达现实的符号体系,它作为一种运用,其结果是产生一个时代的无意识结构,这一结构是隐蔽的,但却是有效用的,这一结构同时需要某种表达方式。而表达现实的语言与现实本身都成为了这一结构的外在效应。发现并表达话语结构并探寻其恰当的表达方式,成为了人文学科的基本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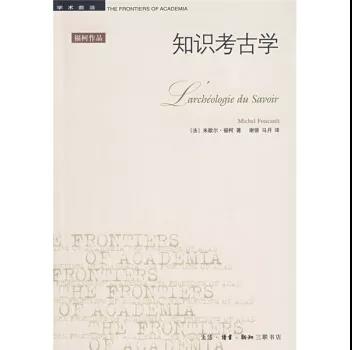

《知识考古学》 福柯
在当代大众文化形态中,只有电影需要肩负这样一种表达话语结构的责任。因为,在多样的媒体文化表现手法中,电影是唯一可能成为一种哲学的表达方式的媒介形式。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指出,“电影是一种哲学情景(situation philosophique) ,抽象来讲,一个哲学情景就是术语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术语表面上看没有关系。一种哲学情景就是陌生术语的相遇” (4) 。这一情景,更进一步说,即意味着“必须思考事件,必须思考例外。我们应该知道对那些不普通的事件说些什么,应该去思考生活的变化” (5) 。这种断裂式的哲学情景本身,也是福柯的话语结构试图表达的另一个面向。支撑话语理论的历史观是断裂的,而非连续的。因此,作为特定时代之无意识的结构,话语所表达的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更多只是对一个溢出到原初的历史叙事之外的事件的可能性。对于福柯而言,话语的实践所带来的是彼此异质的知识型的考察,而对于巴迪欧而言,则为不同哲学情景的发现。电影是通过影像的综合艺术方式将这一话语实践具象化的最有效手段。电影的本质从来不是为了讲述一个完整的、逻辑清晰的故事,而是要表达一种语言与现实背后的话语结构,因此其所显现出的样态反而可能是与现实生活的“陌生化”,换言之,每一部优秀的电影应该构成平庸生活的一个事件,由此激发出一个非日常化的意义(即哲学情景)的呈现。
既然电影与话语结构的建构及其表达具有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共谋关系,那么动漫电影也不应例外。动漫形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电影表达手段,它绝非仅属于低龄群体的审美对象,相反,它的制作方式使其在有限资本支持的条件下创造出可容纳无限的想象力的空间。话语作为一种支配语言与现实的隐性结构,更需要富有想象力的建构方式。将想象力视为知识形成之根基的康德指出,想象力是“即使对象不在场也能具有的直观能力” (6) 。动漫的电影语言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最为擅长表达这种不在场的在场。因此在我们还未有足够的技术支持去拍摄神鬼怪诞之前,动漫是表达这类题材的最好手段。例如在1964年的《大闹天宫》中,美猴王的形象是对于文字版《西游记》的一种不在场之在场化的表达,其所构筑的审美取向一直以来左右着人们对于美猴王的想象,以至于真人版的《西游记》都没有摆脱其基本轮廓。这正是动漫想象力的强大能量。

1964版《大闹天宫》
对于话语结构的建构与表达需要这种想象力。构建即为创造,创造无法脱离想象力的作用,同时在将隐性的结构具象化的过程中,想象力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电影叙事的事件化所需要的一些另类的、富有间离感的审美感受,都需要想象力的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动漫电影有可能成为建构和表达话语结构、抑或说哲学情景的最好方式。
2民族性话语表达方式
并非等同于中国元素
构筑一种富有民族性的话语表达方式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仅关涉到中国动漫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即以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之口号来换取国际电影市场的认可,而更是因为,只有话语结构获得一种真正富有民族性的建构方式和表达方式,我们才可以将只属于中国当下的人的生存状态之独特性表达出来。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思想的趋同等于思想的灭失。缺乏民族性的话语表达方式的中国动漫,只能停留在运用些许中国元素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富有思想穿透力的中国式动漫风格,因此也难有可流传的经典之作。
近年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元素进入动漫电影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趋势。中国故事与中国式画风在世界动漫市场上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卖点。但1998年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只不过是用美国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中国故事,其中除去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被置换成了中国之外,其他所有的对白、音乐、人物性格设定以及故事安排都充斥着美国式的幽默和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叙事方式。这种种鲜明的特征证明,它无非是美国动漫电影产业链条中被“生产”出的又一件同类产品。当然,这对于迪士尼来说无可厚非,因为它从未试图让这部美国动漫去表达中国的话语结构。而它极富有典范性地证明了美国的民族性话语,证明了作为无意识的结构何等强大地将一个纯粹中国的故事融化其中。

《花木兰》
随后,自2008到2016年出品的三部《功夫熊猫》,较之《花木兰》的叙事方式似乎更接近于中国文化。这种“接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对故事发生的自然背景的刻画更侧重于中国山水绘画方式中的写意性,而非写实;其二,以巧妙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中“空”之思想意境进行展现:龙卷轴的秘籍其实不过是一个能映出自己的空白;通过师傅之口所道说出的有关“气”的界定较为准确;已经贯穿其间的带有“坐忘”色彩的修炼方式……所有这一切,都为这部讲述中国功夫的影片涂抹上了更为深邃的中国文化的底色。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只能将其定位为带有浓重的中国元素的美国电影。原因在于,首先,所有这些元素,中国的服饰、山水、功夫、饮食等,对于展开其所要讲述的故事而言都具有可替代性。它们是言说故事的言语(parole)。其次,熊猫阿宝的故事展开,所遵循的不过是一个美国成长类故事所一贯具有的基本套路。在每一集里,阿宝都需要一个与之对立的邪恶力量,并在与其对抗的过程中获得自我进步,这一故事模式自电影《狮子王》直到2016年口碑爆棚的《疯狂动物城》从未改变。我将这一模式视为言说故事的语言(langue)。在语言学中,言语可以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即转变不同的言说方式,但不管它如何变化,其基本的语法结构(语言)是不会改变的。当我们洞察到这个“变”与“不变”,就已触及到了美国的民族性话语结构:这一结构具有希腊悲剧式的壮烈,其间总是回荡着一种个人化的英雄主义基调,并最终往往通过落脚到“认识你自己”这句德尔菲神庙上的格言,来实现自我,完成叙事。

《功夫熊猫》
如果我们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来反观当下中国动漫电影的现状,会发现中国的动漫电影与这些美国人所拍摄的带有中国元素的动漫作品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2015年的《大圣归来》曾经创造了中国动漫票房的一个新高度,其制作之精良与故事编排之丰富也得到了专业人士的普遍赞誉。但这部电影仍然没有为构筑独属于中国的民族性话语提供可资借鉴的有效路径。《大圣归来》仍是一部仅仅带有中国元素的美国式动漫电影。它一方面继承了美式的话语结构方式,即正邪对立分明,解决极为简单(邪不压正) ;借助于佛祖的力量让原本已经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重新回到原点,再一次开启其成长性的发展历程;而且更为吊诡的是,这一电影中出现的中国元素带有过于浓重的西方色彩,如作为邪恶势力的山妖全无中国文化中对于“妖”的审美取向,而偏重于“怪”,且其形象设计更偏向于西方文化对于“怪”的想象,全无中国特色。与之类似,美猴王的造型也失去了《大闹天宫》的版本中固有的意象模型。后一模型之所以堪称经典,是因为其带有某种类似京剧脸谱的审美旨趣,更富有写意性。《大圣归来》中那个更为立体的美猴王,拥有倒三角式的健美形体,用中国的语言讲着美国式的幽默。这种文化意象的错配,虽可能会更好地迎合全球一体化后的市场需求,却无疑正在将中国的民族性话语建构与表达引入到后殖民主义之歧途。

《大圣归来》
构建一种真正富有民族性的话语及其表达方式的意图,其困难之处在于,动漫主创人员对特属于“当下中国”这一特定时空关系所彰显的精神缺乏一种理解能力,甚至缺乏追问这一精神究竟为何的勇气。当下中国所蕴含的精神,不仅意味着它是中国的,同时更是意味着它包含着对“当下”这个时间节点的反思和批判。1988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部唯美的中国水墨动画片《山水情》,其意境与画风都带有极为纯正的中国特色,在业内获得极高的口碑,但观众却对其所知甚少。这不仅因为它过于抽象化的表达方式———全片没有一句台词———而更在于它用唯美的水墨画面所刻画出的仅仅是一个空间中的中国,而没有时间(即当下)中的中国。它所讲述的故事如同一幅古画置于观者的面前,可欣赏,却缺乏感同身受的触动。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动漫而言,要想建构民族性话语及其表达方式,以下两条道路都是走不通的:借助于西方人的审美旨趣讲述中国故事,这只能让中国故事沦为可置换的中国元素;仅用传统中国的方式讲述传统中国的故事,完全无视中国现代性发展与传统之间的断裂,对其间所生存的人缺乏切实的关怀,那么最终也将不过是让中国的动漫电影变成为仅供博物馆陈列的古董。
3《大护法》建构及表达
民族性话语的尝试
面对这一困境,我们尝试走出第三条道路,回归到对当下中国之精神的理解抑或追问。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理解与追问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并不能说出中国的民族性话语及其表达方式究竟包含那些方面,因为它正有待我们的创造,这一创造首先意味着要从既有的全球化话语语境(对于动漫电影而言,这一话语以美国式话语与日本式话语为主导)当中溢出,成为一个哲学情景,一个例外。换言之,真正的、富有影响力的话语结构的建构同时必然带有先天的民族性。其次,从这一故事架构当中应能透露出对于当下人们生存状态的反思和追问。最终,其故事的形象设定,应是在综合性地融合不同的中国元素基础之上而进行的一种新的创造,而非抽象化诸要素的集合,就像《功夫熊猫》中将包子、功夫、熊猫所进行的简单相加那样。
就此而言, 2017年由不思凡原创的动漫电影《大护法》成为一种典范,彰显了中国动漫电影的民族性话语及其表达方式之建构的一种可能性。

《大护法》
这是中国动漫电影史上第一次自觉强调分级的动漫电影。它宣告了中国动漫电影自觉的成人化取向。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动漫电影试图担当其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责任,成人化的取向是其必经之路。而《大护法》的成人性并不仅仅在于它为数不多的情色镜头与大量的血腥屠杀,更直接地表现为由故事中诸多隐喻所构筑的对当下时代的反思和批判。隐喻的表达方式所必然具有的敞开性阐释空间,使其构筑一整套独特的话语结构成为可能。因为在这个空间中,表达者(语言)与被表达者(现实故事本身)都不过是这个结构中的一种可能性,而隐喻让这种显现的可能性仅仅表现为诸多可能性之一。于是,可说的、已说的与未说的都以隐喻的方式得到了丰富的内涵。它所构筑出的些许思想,有可能成为当下中国较为独特的一种话语结构及其表达方式。在此,我将从以下三个隐喻入手,分析其所敞开的探索。
隐喻之一:大护法。它的造型极为独特,因为其无原型,所以充满阐释的张力。红色的外衣,配合背后的乌钢杖,成就了一个近代中国革命主题的具象化显现方式。它的身份以及其所拥有的让它自己都感到害怕的暴力能量,一方面,彰显了革命的合法性:思想者并非执著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而更是要改变世界的行动者;另一方面,其对于暴力自身的反思精神,又让其成为一个最为清醒的革命者。“他看到我了,你觉不觉得,那更像是一步步从黄泉路上走来的鬼。杀掉他看到的、厌恶的和恐惧的一切。他靠近我们,瞄准我们,子弹穿透我头顶的木板,打爆我凉透的脊背,扑倒在你面前,死相难看……”这种场景的描述出自大护法的自言自语,如同有一面镜子树立在暴力残杀的面前,大护法成为一个可以看到自己死亡的革命者。于是,他并不是一个仅仅为了屠杀而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他在整部电影中的角色设定只有杀戮,我们甚至无法辨认它的面孔、身体、性别,它原本是一个抽象的暴力的象征物,但却被思想承载,所以他有痛感:“总共断了十一根肋骨,好久没有这样有活着的感觉了,痛得那么透彻。”因为有这种彻底的痛,所以大护法成为了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整部故事正是以这个有血有肉,却无形无相的大护法的介入(这是革命者存在于世的唯一方式)为视角展开其独特的话语结构。因为是介入式的展开,叙事因此是片段性的,并无任何前情铺垫,红色南瓜般造型的大护法突然出现在一个群山环绕、却诡异异常的小村庄之中。这一表述方式,虽使得故事的展开略显突兀,但恰好成就该故事建构独特话语及其表达方式所需要的间离效果。观者无法被带入到这样一个怪异的故事当中,却作为彻底的旁观者为这一故事任意增加了多个想象的维度。因此,大护法的形象设定以及其作为故事主线的构造方式,为这部电影提供了建构独特话语结构的可能性操作。
隐喻之二:花生人的诞生秘密。每个花生人带着虚假的眼睛与嘴巴,缺乏彼此之间的语言与交流。而语言,在当代哲学中正是“存在之家”。没有语言,意味着没有对存在的追问与反思。于是,所有的花生人拥有毫无辨识度的面孔与身躯。它们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常人”,也是尼采意义上的“末人”。它们正是身处“当下”的我们的一种生存境遇:有着作为存在者的肉身,却似乎缺乏追问存在本身的能力。因此,花生人与那些可被生产出来的物品毫无区别,是可以用“种植”、“培育”与“收成”等词汇来形容的。这种将生命纳入到可管理、可操控的情景,被福柯等当代思想家用“生命政治”概念来加以讨论,它让生命本身变成一种权力机制可以操控的东西,生命权力由此而诞生。在福柯那里,这种权力“即一套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类这个物种的基本生物学特征成为政治策略的对象,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策略的对象,或者换言之,说明了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从18世纪开始接受人类是一个物种这一基本的生物学事实的” (7) 。在这一生命政治的操控下,有了所谓的“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预期、种族”等一整套“政府管理实践”的产生 (8) 。这一对现代体制的强烈批判也切中当下中国的现实。这一抽象的理论,在这里通过花生人诞生的秘密以童话寓言的方式得到了最为直观的表现:花生人是用其所食用的蚁猴子作为胚胎在实验室中成长起来的。分别作为先知与觉醒者的隐婆与小姜洞察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了诸多关于存在的追问,这一追问始于小姜与太子和隐婆之间的言语沟通:“我们是谁,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隐婆揭示了残忍的真相。这种存在主义哲学层面上的提问,是破除“常人”与“末人”的平庸化生存境遇之魔咒的杀手锏。觉醒在所难免。
隐喻之三:花生人的暴动。作为彰显残酷美学的一部动漫作品,觉醒后的花生人并没有如同美国动漫电影的话语结构一般,仅仅完成一次正义战胜邪恶的对决。相反,觉醒了的花生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对于那些还未觉醒的花生人的屠杀。这种以暴制暴、胁迫性启蒙彰显了人本性中的恶。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大护法》中的人物性格设定都没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大护法的冷静与残暴,太子的善良与软弱,无脸杀手罗单的冷血与柔情。所有的人物性格都是丰富的,而这恰是文明社会中的人们所具有的真实的复杂性。
用种种隐喻所表达出的略显怪诞的故事,因其对白中所提出的问题准确地切中当下人的生存境遇,反而成为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话语结构的成功尝试:它模糊的历史时间,恰好让人跳出任何一个时期传统中国的文化固守,直接将其视为一种对当下时代的反思和批判;它的语言是真正中国式的语言,简短而有力,没有太多的调侃式的幽默,却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木讷与内敛及其语言魅力;其动漫所采用的水墨画风,丝毫没有影响到该剧所试图表达的现代性批判,为中国传统动漫技法与现代思想找到了一个恰好的结合点。除去大护法的独特造型,其中花生人的造型也颇具中国制造的烙印:光头造型让人想起1982年出品的《三个和尚》中的和尚造型。概言之,《大护法》以一种独特的当代中国的话语方式讲述了一个古代中国的故事,同时让古代与现代都得到了一种毫无违和感的表达。其中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民族性话语结构的创造。这种结构的首创性和独特性使得其所讲述的故事不再仅仅是中国元素的堆积,而变成了中国人理解世界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其间充斥的暴力与性,或许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东西,却成为当下中国无法回避的平庸之恶。
从《大闹天宫》到《大护法》,中国动漫电影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大闹天宫》可以作为民族性话语表达方式之建构的开端,而《大护法》却绝非其终点,它只能是一个小小的节点。电影作为一种必须与资本联姻的艺术形态,却从不依赖于资本去获得其独特的民族性话语的建构和表达。
拍摄于1964年的《大闹天宫》,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一种创造。但由于其准确把握了那一时刻“当下中国”的时空特质,并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从叙事到审美形象的设计方案都符合那个吐故纳新的时代之精神,从而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虽带着中国传统京剧脸谱、却具有彻底的革命性的美猴王,它成为了60年代新中国建设与时代精神的具象化表征。它之所以成功并不可替代,正是因为它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话语。
时至今日,从《大护法》中,我们隐约看到一种符合当下中国的新的民族性话语结构及其表达方式的出现,但其形态仍然是幼稚的、有待成熟的,这主要表现在它的叙事方式的过于含混。隐喻化的叙事既成就它的阐释空间,同时也成为阻碍大众理解它的一道屏障。缺乏一定理论背景的观众,可能无法抓住这些隐喻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对白与独白中的思想性表达得过于隐晦,很多跳出了既有合理情节的要求。例如无脸杀手罗单死前突然喊出:“妈妈要下雨了。”作为一部独立电影,这种无厘头的台词不仅没有起到提升思想的作用,反而扰乱人们对电影本身的理解。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作者本人想说出来的要远远多于其通过这部动漫的情节所能够表达的,作者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失去了掌控能力。
另外在人物设置上,与罗单拥有着一丝暧昧的美女,除了被诠释为成人动漫所不可缺少的“性”的象征之外,并未显现出其他作用。如果这一角色在随后的续集中仍未有其他意义,这个人物的设定难免陷入刻意为之的做作,在某种意义上反而降低了本片的艺术水准。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了当代动漫电影的制作总是需要在艺术与票房之间挣扎的现状。但不管怎样,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总是要有它独特的群众基础,当它不能被大众真正理解之时,其固有的艺术性,即对当下的批判与反思也将变得无效。这是《大护法》在另一层面上失败的原因。真正富有民族性的话语结构首先应该是该民族大众所能理解和体验的,这也应当是《大护法》的后续系列以及所有试图通过动漫电影构筑民族性话语的作品有待努力的方向。
注释
1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6页。
2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3 参见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 (5)李洋选编《宽忍的灰色黎明——法国哲学家论电影》,李洋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第5页。
5 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6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trans. Graham Burchel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6.
7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 Graham Burchel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