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薇
摘要
道德超越性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特质。在如何理解超越的根据、途径和目标上,儒家主张源于天赋良知的自力成圣论,基督教坚持源于他力救赎的因信称义论。关于先验善性与天命之谓性的设定是自力超越的可能性根据,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反省内求之路是自力超越的途径,内圣外王的天人合一之境是道德超越的最高目标。这一过程是回返原善开显良知与恭顺上天契合天命的统一,即内在而超越,取向知行不二,应该与能够合一。关于悖神的罪性论及其无能为善的设定是他力救赎的神学根据,打开信仰之门走上悔罪之路是接受神圣救恩的路径,因信而称义是道德超越的目标。这是在神人之间展开的启示—信仰—救恩的过程,即外在而超越,凸显知和行、应该和能够之间的距离。基督教关于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与神圣之维的彰显,可以提醒儒家对于人的有限性存在处境保持警惕。
“
关键词
自力与他力; 善性与罪性; 良知与信仰;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按照康德的说法,人在本质上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乃是两个世界的公民,既是自然世界的一员,遵守现象界的必然法则,又是自由世界的一员,遵守本体界的道德立法。这使得人的存在在受必然性约束的同时,不会像动物那样完全沦入自然本能的生存秩序,相反能够生活在道德法则的自由世界。所以尼布尔说,人是一种兼具自然依赖性和精神超越性的双重性存在者。由此推知,成全一个道德的人意味着可以突破人的动物性生存的限度,进入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之境。这就构成了人类特有的“道德超越性”的观念。那么,如何理解超越性的根源或依据、路径或模式、旨归或目标呢?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各种伦理传统都有自身独到的见识。儒家可称为基于天赋良知的自力成圣观,基督教可称为源于他力救赎的因信称义论,二者构成鲜明对比。这一话题一度受到学界的热烈关注并引发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的争议,如今沉息下来后,我们不妨再做一番检审和参较。
1
众所周知,儒家是一种典型的德性伦理,讲究修身养性,成德成圣,这是一条自力修养之路。对此,儒家充满信心。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也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问题是,儒家何以这么自信,自信的理由何在?换言之,通过自力修养实现道德超越何以可能?这就需要检审道德超越的可能性根据及其实现途径。

首先,儒家的道德论建基于人性论。如何理解人性的本然和本源,决定着道德成全之路将会如何展开,道德超越采取什么样的模式端赖于对人性的理解。关于人性,儒家的主流观点无疑是一种先验性善论,孟子可谓典型代表。他以孩童落水致心生恻隐,说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为“善心”。“善心”有四: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其中恻隐之心是根本。在孟子看来,人皆有之的“四心”乃是人性里先天潜在而非后天学来的四个“善端”,即仁、义、礼、智之四个善的起点。“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而矣”(《孟子·告子上》)。这表明,人心天赋善心,人性天赋善性。孟子称这种天然具有的善心和先天而备的善性为“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王阳明也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
为了说明先验善性及其良知良能乃是人性的普遍性,孟子还从“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的类比逻辑出发予以论证。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人心喜好理义犹如人口喜欢美味,自然欲望人所同之,明理好义也是人性皆备皆能,圣人与常人无异,区别仅在于“先知先觉乎”内心所有而行之。

正是在先验性善论的基础上,儒家打通了一条自力修养的道德超越之路,在此,天赋的良知良能构成了道德超越的内在性和可能性根据。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良知良能乃是一种纯粹德性而非纯粹知性的存在。不用耗费思量的功夫、自然而然即能知的“良知”不是指向外物见闻,而是指向善心直觉,也可称作“良心的觉识”,是一种“德性之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同样是一种道德性的先天能力,与良知浑然一体,即知即行,知行不二。正是根于人性里先天存在的知善行善的良知良能,使得人凭借自身的道德努力成全一个道德人格有了内在的可能性,而儒家的道德自信也是建立在这一逻辑基础上的。否则,人性人心若根本是恶性恶念,也就失去了从内在自我的修养开始而走上一条道德完善化之路的可能性依据了。不过,良知良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善的“基质”或“端点”,还需要开掘之、扩展之、发扬光大之。因此,道德修养也就有了必要,并展开为一个不断扩充良知良能的完善化过程。
这里我们发现了某种不可避免的解释学上的循环,一方面与性善不可分离的良知良能是道德自力的内在根据,具有某种本始意义;另一方面,只有在良知良能的基础上才可能的道德自力,回过头来又成为开发或开显良知良能的过程,因为良知良能作为人性善的先天禀赋,并不意味着每个现实的个人都已经是一个道德完备的人,而仅仅是一种潜质和潜能,尚需要进一步开发和彰显出来。
那么其次,这是一个怎样的道德自力的开显过程,这一过程的目标又如何呢?按照儒家的观念和思路,这是一种反省内求、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活动过程,目标在于进入成仁成圣、内圣外王的天人合一之境。在此,成人成德既是一个反省内求、回归和开显源始善性的过程,也是一个秉承上天、契合天命的超越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进一步关涉到儒家对于人之为人、性之为善的终极来源或终极理由的确认。假如先验善性的终极根据在天和天命,那么,回归和开显源始善性同时也就是恭天顺命和知天知命。事实上,这正是儒家的思路。
在儒家看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禀天命所赋为性;天人一体,性命合德。故而人之为人本于天,人道上接天道,人性上承天命。那么,天之何所然之,又何所为之?一言概括,天乃自然之基,德性之源,有生生之仁,本真之诚。而“人”正是这天地生生不息、造化不已的好生之德的产物,也是这天命所赋之禀的所是或所在。既禀受了阴阳之气、四时之化,也禀受了生生之德、仁善之性。对此,子思说“天命之谓性”(《中庸》),孟子讲顺受天之“正命”存以为性(《孟子·尽心上》)。朱熹释之曰:“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而“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故“人之性所以无不善”也[1]。在注释《大学》“明明德之道”时又言:“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1](4)焦循在注疏《孟子》时也阐明,人之“赋禀”由“天”而来,此之谓“性”。在“天人赋禀之际,赋乃谓之命,禀乃谓之性”。人性之禀受于天命之所赋,故言“天命之谓性”,亦即“天命之性”。天地之位包容万方,含有“元亨利贞之德,是故天地之性善也”;人性禀受天命所赋,“有仁义礼智之德”,是故“人之性善也”[2]。正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天有好生之至德,人有好善之至性,此即是“仁”。仁者人也,仁者天也,仁者天人合一也。可见,先验性善论的终极根据在天和天命。仁为天人之本意味着天人合德,既然如此,修身养性、成仁成德之路便展开为返观内求之路,因为善性在内,天赋具备;又实现为达天契命之路,因为天命之谓性,天人合一。于是,这条道德超越之路无需求诸外,完全可以依靠自力修养来实现。“良知良能”从本源上说来不过是对“天命”的直接觉识和领悟,而以良知良能为内在根据的道德超越的实现途径,便是“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过程。如果说天命之谓性或立命存性是为道德自力超越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性善论根据,那么,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则为道德自力超越所以可能的功夫论阐明。下面再稍加展开以论之。
从孔子来看,“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可视为这一道德超越的存在论和践行论表达。“天命在身”可谓是孔子的一种存在论情怀,而“仁”在根本上意味着和天命相与之道。这“道”(亦“仁”)既是天人相与的路径和方式,实为一种道德实践,也是天人相与而展开在人身上的天之所命,实为“诚之者人之道”的根据即“诚者天之道”,还是恭天顺命之人的本真所是,实为一种德性之在。故而天命与人性、天道与人道是合其德而共其在,这必然使道德超越的过程同时展开为一条天人相与之路与反省内求之路。
从孟子来看,这条与天命相与的内求之路被更加清晰地阐释为知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双向超越之路。一方面,这是一条“内知内证”之路,体现着道德超越的内向性。我们看到孟子以心释性,进而释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如果说从存在论的顺序上讲是从天到人,从天性好生之至德到人性好仁之善心,由天而性而心的话,那么,以心释性则是从认识论的顺序上讲,认识了心便知道了性,知道了性便明白了天。如果认识到心之为善,也就可以发现性之为善,进而发现天之为善,即由心而性而天。不过,这个认识论的顺序绝非康德式的认识论那般纯粹,而是既和道德直觉、心理情感交织在一起无法剥离,也与身体力行的修养功夫一体化之,毋宁说就是功夫论的,知行合一才是其最重要的旨趣和目的。所以“尽心—知性—知天”的认知取向不在于认识论的理论之维,而在于实践论的道德之维。通过道德自力,向自身回返,回到本然之性,回到性之所出之命,这就是存发善心,涵养善性,体悟天命,进入天人合一的源始亦即终极之境。
在此,内知内悟、内求内证的道德努力根本上是天人相与的体认过程,儒家所谓内在性命其实就是人之性和天之命的统一体(仁)。这样看来,如果离开自身向外寻求器物和功利的世界,恰恰是沦入天人分裂、人格失落和工具化生存;如果回返自身内求心性,便回到了与天命同在的本源处。这里我们将尽心—知性—知天或存心—养性—事天称之为“道德超越的内向性”。

另一方面,道德超越还有一个由内及外的开显或外推的意义过程,即从内在性命开始,从良知善端开始,将之逐渐发扬光大直至充塞天地之间。这是一种立人极以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之道,也是正心、诚意、亲亲、仁民、爱物的成圣之道。正所谓入俗又超俗,超世又入世,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因而内求回返的同时也是为了推内于外,将仁善的心性人格化为外在的人伦王道,从而完成在身的天命,这可以说是“道德超越的外向性”。
集超越的内向性与外向性、知与行于一身便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圣人之境。儒家传统历来把“圣人”作为人生修养内外兼备的完美人格和理想境界。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境界呢?概而言之,从性而言,圣人可谓至性,仁之至也;可谓至人,人伦之至也。从行而言,圣人尽性守仁、应天而化、参天赞地、施教人间,可谓“天人”。由此可知圣人具备两个元素:内有至仁之性;上应终极天命。此也正是孔子“与命与仁”的精神诉求,亦即知天乐命和守己抱仁的统一。
分而言之,三代圣王为儒家提供了最初的范型。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赞之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子思盛赞圣人之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庸》)。孟子则认为,圣人以“仁德”为“天爵”和“安宅”,出乎仁义之至性而行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朱熹注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此则圣人之事,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1](274)正是由于出乎人性之至,故而能够游于天人之际,“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此种境界可谓“天民”。“天民非一国之士”,“其所在而物无不化,唯圣者能之”[1](347)。圣人无迹无滞大而化之于天下万物,内尽心性上达天命,与天合德能居“天位”至尊而无敌于天下。是故圣人亦天人亦仁人。
不过,作为天人之际的先知先觉者,圣人所性圆满无缺,一言一行自然中道,但常人是后知后觉者,虽也性善,却因后天气质之性有清浊,使得先天之性未得以全,需要修养回复其性,而后才能成圣。正所谓:“性者,得全于天,无所污坏,不加修为,圣之至也。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1](349)圣构成了儒家超越追求的目标或境界,而成圣之道便是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过程。
孔子不自圣,却可从其自述中看出成圣之路:“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成圣在孔子不是顿悟,而是不断摆脱外见,洞识天命和本己,直至自由随性,发之于仁、中之以礼、应之以天的圣人之境。孟子尽性—事天的成圣之路是一条知行合一之路。依照朱熹的解释:“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故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己矣。”[1](327)知行不离不分,知心要存心,知性要养性,知天要事天,做存心养性的内求功夫,也是做事天的超越功夫,在扩充善心、回返善性的道德修养中走向天人合一之境。
尽性—事天的成圣之路还表现为一条由己及人的入世之路。《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5)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整个修齐治平的过程中“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己成己。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只有成己才能成人,只有内圣才能外王。自身不正,无以家齐国治天下平。那么如何修身修己呢?这就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只有穷究物理之极,才能知无不尽;知无不尽对明德有明察至见,方使意诚心正。心正则身正;身正则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过,在《中庸》里将“何以修身”倒过来叙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1](30)将两篇结合起来可以这样理解:注目高远,立足脚下。一方面只有视界高超,才能跳出小我的限度,将自身置于天地之间和人人之间,自我修养才会确立起高远的目标,这是由天到人、由人到己的远视收缩之路。另一方面修养践履又必须从自身开始,正心诚意,存心养性,身正而行,出乎仁止乎礼,一步步向外拓展,方可尽人伦,事王道,通历史,赞天地,这是由己到人、由人到天的近行扩展之路。从哲学的高度来讲,人由天生,性自命出,天和天命乃人性存在的本源,养性修身就是恭天应命,因而若昧于天命不知,养性修身也会本末倒置而无以正成。从天到人到己可谓一条存在论意义上的修养之路。反过来,修身之行不能不从自己开始,然后由己推人、由内到外,则可谓一条实践论意义上的修养之路。两路为一,一体两面。
总之,人本于天,天命在身,立命存性,性善先天。在天赋良知良能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道德超越;超越的目标在于成就圣人之境,实现超越的道路在于尽性—事天的天人相参和成己成人的入世努力。
2
如果说儒家坚持欲仁得仁,因而走上一条自力修养以成圣的道德超越之路,那么,在基督教的视镜中情景完全不同,用保罗的话来讲,欲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新约·罗马书》,7:18),因此走上了一条相反之路,即依靠神圣的他力拯救,打破罪与恶的束缚,在信仰中使灵魂重生,以实现信仰基础上的道德超越———因信称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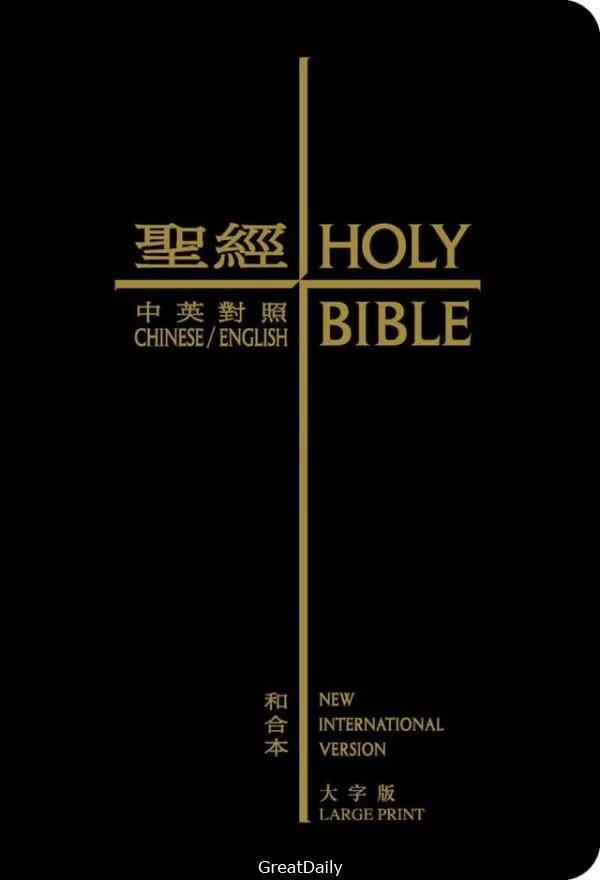
不同于儒家自力修养论的基石———人性善论的预设,基督教的他力救赎论则建基于人性罪论。“罪”(sin)是基督教的独特观念,源自 “创世—堕落—救赎”的神学语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肖像用泥土创造的,既具神的形象,有灵魂有精神超越性,又是被造者,有肉身有自然的有限性和依赖性。他就活在无限与有限、自由与自然、超越与限制的交汇处。“当他处在最高的精神地位时,他仍然是一个被造者;而在他的自然生活的最鄙陋的行为中,他仍显示出若干神的形象。”[3]肉身性和灵魂性、自然性和精神性的双重统一构成了人的基本身位。正是在神的形象和自然形象、精神超越性和肉身有限性的内在张力及其作用下酿成了人性的罪性。《圣经·创世记》里人类始祖罔顾自身有限性的存在,试图拥有上帝一样的智慧,违背禁令,偷吃智慧果,受到惩罚,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提供了“第一罪”的原型,意味着人类最初的堕落,此后的人类无不共同承负了这一“原罪”(originalsin),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就是从罪开始的。罪性成为人性里的根性,堕落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可见,“罪”是基督教关于人性的基本预设,“恶”是关于人的现世处境的基本判断。
在此,“罪”首先意味着人与上帝之间的疏离状态。在希伯来语中,罪(chata)的原意是射箭偏离了目标,这里意味着人偏离了上帝,迷失了自身的崇拜对象,导致人与自身的存在本源和价值本源的断裂。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是:“罪都是因人远离真正永存的神圣之物而朝向可变的不定的事物。”[4]所以罪是一种在人神关系中构成的根本性的生存论之罪,一种“宗教性的罪”。在这种宗教性的生存之罪中,人以自身为中心取代上帝中心,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取代上帝的意志,企图僭越神的地位,使自己成为神。然而,使自己成为神,不仅没有真正确立和维护人之为人的存在尊严和正当位置,反倒损害了人的如神的形象。其次,罪还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人和人的关系发生偏离、扭曲和异化,导致人们之间的互相关联的断裂,这就是恶,恶带来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所以罪也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构成的一种基本的生存论之罪,它是一种“不义”,一种“道德性的罪”。在这种生存的道德性之罪中,人以自我存在为中心,将别人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表面上肯定和抬高了自己的人格地位和价值,实际却在本质上无视人的尊严,亵渎和践踏人格本身,最终导致对人的关系性存在的否定。如果说宗教之罪是在扭曲人的本源性生存,那么,道德之罪就是在扭曲人的现实性生存。实质上,正是由于人与上帝关系的偏离,才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的偏离;正是由于人疏离了生存的本源和依据,人才在现实生存中发生人与人的关系的失序。所以宗教之罪是道德之罪的根源,道德之罪不过是宗教之罪的延伸。如果说人性是恶的,则根本上源于人性是罪的;如果说人对人犯了罪,那是因为人先对神犯了罪。
人何以犯罪?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滥用了自己的意志自由,意志自由与罪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按照基督教的观念,人是上帝的最高造物,禀有如神的形象,被赋予了意志自由,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和权力。人本来应该依从神圣的律令去选择一种自由而善的永恒生活,但是始祖滥用自由对上帝忤逆犯罪,其罪责自负。正是基于意志自由的设定,基督教既维护了神正论,又得以将罪问责于人,人要自己为自己承担罪的责任。这个罪责首先是对神的,然后才是对人的。就对神而言,始祖的罪作为第一罪对于后人来讲便构成了原罪。

在理性的视野中,无论始祖犯下原罪,还是人类共担原罪的圣经神话,我们都无法从历史的意义上,而只能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来对其进行解读。亚当之罪作为人与神之间的疏离和背离,不是一般的罪,实是“人之为人”之罪。正是从走出伊甸园那一刻起,真正的人类史才开始,真正的人类生存才出现,而人的这一历史生存正是一个负罪的时空结构。究其因,恰恰与意志自由或意志自主脱不了干系,而意志的自由自主性正是人高于自然万物的精神超越性。可是,人毕竟又是自然的一员,无法完全跳出自然性而成为神。亚当误用意志自由试图变得拥有神一样的智慧而犯原罪,实际昭示着基督教关于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及其可能命运的理解。它意味着人性存在的精神性和自然性的内在张力使人无法置身于一个纯粹善的神性的生存结构中,而是随时生活在善恶交锋、神兽交战的生存状态中。罪正是对这种人类独有的生存状态的深层刻画,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欠缺的。而这一生存之罪态恰恰又是在神圣之维作为最高价值依据的参照下、在人神关系的框架内得到确认的。
在这种思想语境下,基督教的超越问题在根本上是如何跳出罪的束缚,从堕落状态中解救出来,重新修复人神之间的和谐关系,回归与上帝本源之间的存在论关联。这是整个生命的改变,由向人活转换为向神活,道德上的超越是其中的一环,严格说是它的结果。为此,基督教提供的是一条依靠他者之力,在神圣的恩典和启示下因信称义的拯救之路。这里包含着自上而来的神的外在救恩和自下而来的人的内在信仰,而打通上下的途径则是神圣的启示,耶稣基督便是最大的启示,是上帝之道成肉身。基督十字架是罪的符号,是救的象征,是重生的标志,对基督上帝的信靠和追随便是“因信称义”之路。
对于基督教来说,何以非要依靠他力救赎?除了创造论和基督论为之提供了源始的神学依据外,更为关键的理由在于罪性使人的道德实践力受缚,将人抛进了在道德上的不自由状态。换句话说,人的自由意志因罪性而失去了自主向善的自由能力,除非神性的救赎,否则人便无能自救。在这方面基督教对于人性的幽暗面有着深刻洞察和体认,保罗曾做过非常生动切身的描述:“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作的恶,我倒去作了。我若做自己不愿做的事,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律,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发觉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征战,把我掳去服从肢体中的罪律。我这个人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罗马书》,7:18-24)
透过保罗经验里的身心交战、灵肉冲突的内在挣扎,我们看到罪性使人性沦入自我奴役自我受缚的状态。这与儒家道德自力所体现的自己把握自己的道德自信和道德自由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保罗的经验来讲,受困于罪性,人意愿行善,人应该行善,人知道行善,可就是没有能力行出来。在知与行之间、应该和能够之间彰显出巨大的距离和反差①。相反对于儒家来讲,知行不二,应该和能够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王阳明《传习录》)。真知和真行是一回事,因为此知不是他知而正是良知,良知即良能,本身就包含着行动的能力,应该的就是能够的。于是为仁由己,欲仁得仁。可是对于强调罪性的基督教来讲,正如奥古斯丁的发问:“怎样得救呢?他们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吗?自然不能。人既灭亡了,那么除了从灭亡中被救出来以外,他还能行什么善呢?他能靠意志自决行什么善吗?我再说不能。事实上,正因为人滥用自由意志,才把自己和自由意志一起毁坏了。”[5]路德也说:“要是没有上帝的恩惠和圣灵,自由意志就只能作恶犯罪。”[6]加尔文说出了更为严厉的话:“除非有恩典的帮助———那藉重生只给予选民的特殊恩典的帮助,人就没有为善的自由意志。”[7]因此结论是明确的,要摆脱这种不自由的处境,他力救赎成为必然之路。罪中人的无力自主向善需要神圣力量的人性论根据和人类学理由。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神圣力量的救赎而向善呢?奥古斯丁说:“一个人若非凭着信仰被称为义,又怎能过上义的生活、行出善事呢?”②因此,打开信仰之路,“因信称义”是基督教提供的得救方案。

站在宗教哲学的立场上解读,这里的得救作为一种神性的“救恩”来自存在的本源,对存在的本源发出的施救只能采取信仰的方式去领受之。这种信仰被蒂利希称为面向终极而开启的“超越行为”,超越了一切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因素,指向了“终极关切”。信仰者将自身投入进去,在信靠和献身的状态里,整个生命为终极实在和终极体验所统御。这样一来,信仰在根本上关涉着存在还是虚无、生还是死的问题,因而也被蒂利希称为 “生存的勇气”[8]。正是凭着这种生存的勇气打开了一条因信称义的路。
因信称义是在追随耶稣基督的道里重生,而后得以重塑德性成为义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这是一次通过信仰实现的朝向上帝存在的生命转折,扭转了向人存在的自然的生命秩序。但它并不意味着超出了人的现实性和此身性,而是要在信仰救恩里重新安置人的现时性和此身性,变旧人为新人。对基督教而言,只有将神圣的永恒置于当下的内心,以虔诚的信仰跟随神,在世间走一条超世的路,在尘世过一种与天国相连的生活,才能够清洗罪性,净化心灵,守德行善,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使俗世的生活拥有一种神性赞许的价值。因此,道德的生活是在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律法的约束下。信仰是道德的前提,道德是信仰的结果。没有信仰,人在罪性的束缚下是不可能行善的,因为已经丧失了自主行善的实践意志力。只有在信仰中接纳神为救主,更新了的生命才能在生活中结出道德的果子。
在此,善行、信仰、救恩之间的关系是:善行是信仰的结果,信仰由救恩而来。救恩不是由于人的善行,甚至不是由于人的信仰而给予的“回报”,而是一种无条件给予的“爱”的“恩典”。恩典或爱是上帝的出场,具有原初性、在先性、自身性,信仰意味着接受了神赐的爱或恩典,由此带来了新生并因此而能成义。“成义”意味着将“信、望、爱”三种美德集于一身,其中爱是核心,也是对基督徒最高的道德要求。耶稣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戒命。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戒命作为根据”(《马太福音》,22:37-40)。基督教伦理也因而被称为爱的伦理,这种爱的美德由于以神爱为根据和范导以致达到“爱仇敌”的极致,跳出了人性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就像耶稣的教导:“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棍不也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马太福音》,5:4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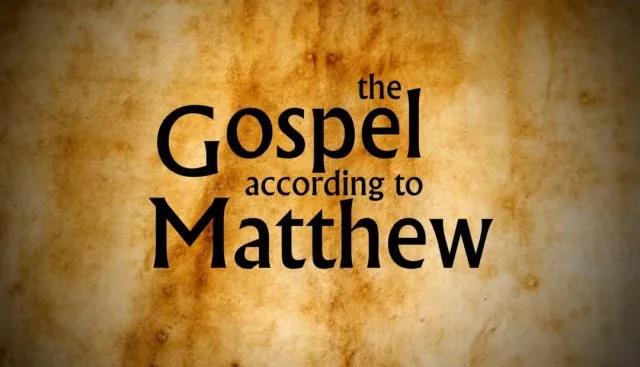
“完全”意味着神圣的在场,然而,爱的完全与神圣只有在超越本然生命的自性欲求,超越任何现世的法律伦常,以神性生命为现世原则的立场上才有可能。依据人性的自然取向,人们必然以自我为基点,爱自己胜于爱他人,爱兄弟朋友胜于爱一般人;爱那可爱的,不爱那可恨的。依据人性的社会取向,人们自然是倾向于持守本阶级、本团体、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以此为轴心衡量和取舍其他的价值。这里的一切肯定都建立在有条件的根据之上,任何一种形态的善都可能以另一种形态的恶为前提,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走向自身反面的可能,其中善恶并存,爱恨两立。而爱的神性是无条件性,爱的完全是爱的绝对,恨与恶在其中永远无法取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为了什么样的爱和善的目标,以恨和恶为手段本身依然是恶。以恶对恶不过是继续为恶,屈从于恶。在爱的神性秩序以外顺从人性的价值选择,无法为沉沦堕落的生命提供真正的道德救赎,这是“爱仇敌”所昭示的“以爱承负恶”或者“以德报怨”的真谛。
可见,基督教爱的伦理不是植根于人性,而是植根于神性。十字架之爱是对人的自然生存结构的突破,而非人性根基上的升华。不是道德植根于人性,人性的罪性使德性无能;而是人性植根于神性,神性支援德性。这种独特的精神性格决定了基督教的道德超越必然是一条他力救赎的信仰成义之路。在信仰中真诚地忏悔和洗罪,而这种信仰在根本上是对于绝对神爱或神恩的信仰,只有在这种绝对的神圣之爱(agape)里,罪与恶才可能得到彻底消解。因为它不是因可爱而爱,而是因爱而使其可爱。所以这种神爱是创造性的,让人重生,罪人变义人,恶人变善人,真正的道德成全才可能。正如现代神学家云格尔(E.Juengel)所说:“罪人因为被爱才变得可爱,而不是因为可爱才被爱”;“上帝之爱不是发现爱的对象,而是创造爱的对象”[9]。
3
综上所述,在儒家传统中,道德超越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自身修持实现与命与仁、参赞天地之境,可称之为自力型超越。在基督教的传统中,道德超越的根本意义在于信靠那个作为创造者和救赎者的神圣力量以解除罪性束缚而成为神眼中的义人,我们称之为他力型超越。其实,这种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在他力的超越中不包含任何自力的因素,反之亦然。无论哪种类型,超越都意味着人的精神性生存可以跳出外物之域和个我之域的限度,走进与本源世界相连的生存之境。而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超越总是离不开主体性的精神活动,无论是自觉的道德修养还是心灵的虔诚信仰,因而都具有主体自我的积极努力,不可能不具有自力性因素;另一方面,超越总是要跳出个体自我的限度,通达某种至上性的本源,无论这种本源是人格性的还是无人格性的,却都不是僵死的,而是包含着内在的生机活力,具有某种 “能动”的意义,或是最为彰显人格性的上帝意志,或是基本不具有人格性的天机、天时、天意、天道、天命等,都会产生某种人力之外的作用和力量,因而在超越之中也都包含着某种他力的因素。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根据主导性的因素和倾向,将儒家和基督教区分为自力型和他力型才是适宜的。
在此,也牵涉到学界一直争论的一个相关问题: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问题。最先应该是在现代新儒学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讨论中提出的一个看法,认为西方文化属于一种外在超越型,中国文化属于一种内在超越型。由是,代表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督教也就被视为一种取向外在超越的价值体系,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则被视为一种取向内在超越的价值体系。但是这种提法受到了种种质疑,如“外在超越”是一种同义反复,“内在超越”则是一种自相矛盾,因为超越的意思就是超出自身、越出向外。[10]到底该如何理解呢?
依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词的逻辑性,而在于它的内涵或所指。任何超越作为精神性的活动都不可能不发生在人的内心,儒家的超越基于自我良知的反省内求自不待言,即便是基督教的上帝所实施的外在超越的拯救行为也需要通过人的内在精神信仰才是可能的。就此而论,超越必然具有内在性,甚至可以说,只有在“内在超越”的意义上才是全备的。而且,即使是基督教的上帝这样一个具备完全的外在超越性的绝对他者,也通过“道成肉身”的方式住在人间,与人同在,这可以看做外在超越的上帝同时也内在于人类世界的一种表达。事实上,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上帝,既超越人间又临在人间。也只有这样,在上帝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之间才能构成生存论的关联。可见,即使将基督教的超越视为外在超越,它也并不排斥内在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儒家的超越虽然采取反省内求的方式,但是在“尽心—知性—知天”或“存心—养性—事天”的链条中可以看到,同样包含着由内而外的旨趣。虽然儒家的天和天命与人合一,但终归不是等同,毕竟人从天而来,人性由天命而出,依然具有某种外在而至上的意义,所以即使将儒家的超越视为内向超越,它也并不排斥外向性。
正如超越的自力和他力两个因素互相渗透一样,超越也总是包含着外在和内在、外向和内向两个因素。任何超越如果只是停留在自身之内,也就称不上超越;任何超越如果不同时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相关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无意义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理解超越的行为过程中“内在—外在”这一环节的内部关系走向时,究竟强调和注重的是由外在而内在呢,还是由内在而外在呢?如果是以“外在而内在”为主导的超越取向,那么可称之为“外在超越型”;如果是以“内在而外在”为主导的超越取向,那么可称之为 “内在超越型”。就此而言,儒家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坚持一条从自我心性到天和天命的反省内求之路,即“尽心—知性—知天”或“存心—养性—事天”,显然是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模式;而基督教在神人划界的基础上,坚持一条从绝对他者的恩典—启示出发,通过信仰—追随基督以获得神圣救赎而重生之路,显然是一种突出“外在超越”的模式。仅此而言,我们称儒家为“自力型的内在超越论”,基督教则为“他力型的外在超越论”。

在上述基础上,倘若我们以本于内的态度对待儒家,而将基督教视为一种外在价值系统的参照,那么可以说,一方面,儒家讲究道德修养的操持在我性凸显出十分卓越的道德品格和自我担当的精神风骨,而反省内求的取向也表现出君子不器、不为物役的高迈和独立,在现代人益呈功利和平庸的生存状态下,这种超拔的人格尤其需要培养和树立。另一方面,儒家的君子追求建基于内在的善性良知和自由自觉的道德努力,然而,正像基督教罪性论所见,人性世界的软弱无能常常使得自我修养之路遭遇挑战甚或失败,这也是康德伦理学之所以有上帝公设的一个原因。如果说先验善性论提供了道德成全的可能性,那么堕落生存处境中的罪性论则揭示了道德实现的严峻性。在此,若将后一种视角作为前一种视角的补充,则基督教的拯救—信仰模式也可以作为儒家成德成人的一种外援路径。
如果说上面是从肯定性的视角来看外向信仰对于内向道德的支持,那么,若从否定性的视角来看,基督教的外向信仰还可以提供另一种支援。人总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者,倘若不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虚妄地将自身扩张为无限的存在之“神”,也会产生自我异化而走向道德的反面,这一点在现代世界得到验证。由是,外在的神圣之维将永远对人是一种警示,它使人谦卑,使人意识到自身生存处境的有限性,从而保持道德上的审慎和约制,以避免自狂和自毁。事实上,孔子也将守仁抱仁的立身实践与天命在身的精神信念统一起来,既坚持为仁由己,又保持对天命的敬畏。这种与命与仁、亦宗教亦人文的精神与基督教并未隔绝。
与此相连,儒家道德自力的成圣之路乃是一个内圣而外王、超世又入世、承接历史王道、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体现着非常突出的政治道德关怀和现世价值追求。这与基督教天国与尘世二分,地上之城无真正正义,唯上帝之城才有永恒正义,因而才是值得献身的最高目的之价值取向表现出巨大差异。一个要在信仰中保持对罪性处境中的现世伦理和政治秩序的神性超越,另一个恰恰要通过尽性—事天的道德努力来投入社会人伦和历史王道。在此,立足于现代视野和传统反思,基督教对于现世秩序保持一种神圣疏离,不失为一种批判之维,可以成为儒家的借鉴。
最后,仍需确认一点,谦卑的基督教精神是要在神圣的救助之下去行善称义,道德追求依然是题中之意;高迈的儒家道德取向是要在反省内求中回归天命之谓性,契合天命同样是儒家题中之意。若说前者在凸显的宗教精神里包含了道德关怀,则后者在凸显的道德精神里包含了宗教关怀,二者都不缺失宗教终极之维和道德人文之维。从“天—人”和“神—人”的整体运思框架来看,无论是上帝创造及其人为神的肖像,还是天命在身及其存天命以为人性,它们都是超验的宗教性信念,并由此以超越的姿态做出人的回应,只是超越的依据和目标不同,采取的路径和方式也有不同。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互参的必要与沟通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05.
[2]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版,1986:435-437.
[3]〔美〕尼布尔.人的本性和命运[M].谢禀德,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9:149.
[4]〔古罗马〕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M].成官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7.
[5]〔古罗马〕奥古斯丁.奥古斯丁选集[M].汤清,等,审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6:420.
[6]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83.
[7]〔法〕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M].徐庆誉,审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171.
[8]〔美〕蒂利希.蒂利希选集(上)[M].何光沪,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266-282.
[9]刘小枫.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792.
[10]何光沪.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M]//陈明.原道.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51.
注释
① 关于保罗意志无能的经验,阿伦特评论道,这种经验是古希腊人所不知的,它源于希伯来人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关于世界的,仅仅是在人自己之内的、自己对自己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发生是在离开了周围一切现象界,只有自身相与的孤独状态的时候,这时候自己和自己思想的对话,才可能发现意志的无能。不仅如此,无能的经验也是在人的意识开始怀疑“你应该”和“你能够”的一致时,自由成了问题,独立自主的意志能力的问题也呈现出来。(参阅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9页)的确,在苏格拉底身上是不存在这种无能经验的,在“知识就是美德”的思路里,知善就可以行善,获得了善的真理的人就是一个有德性的人。理性之维的坚挺排除了意志无能的体验的可能性,因为冷静客观的审视和沉思是获得真理的途径,这与自己进入自己的心灵体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意识状态。只有孤独自处仅仅面对上帝或苍天的时候,才可能将自己生命深处最幽深的一面裸裎出来。
② To Simplician-On Various Questions, in: Augustine: Early Writtings, pp. 404-405,转引自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本文原载于《道德与文明》2016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