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以来,以康德、雅各比和费希特为代表的主观性哲学达到了高峰,出现了以“主观性的形而上学”取代客观的“绝对者”的趋势。黑格尔在耶拿时期以“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问题为主线,批评了主观性哲学将这种同一局限于主观性一侧的做法,通过提升客观性、给客观性以主体地位的方式,尝试着让绝对者与自我实现融合。黑格尔的客观观念论后来遭到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严厉批判,而马克思则再次恢复了客观性的权威。在19世纪前叶,马克思与黑格尔共同形成了与主观性哲学相抗衡的一方。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如果说由康德和费希特所开启的德国观念论传统是一种“主观性(Subjektivitt)”哲学的话,那么黑格尔哲学则是对这一主观性倾向的纠正,黑格尔使德国观念论传统发生了客观性转向。而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不满意黑格尔绝对精神对自我意识的压制,又通过对黑格尔客观观念论的批判,使德国观念论重新回到主观性的轨道上来。青年马克思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原本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但在与该派其他成员的论战当中,逐渐放弃了主观性的立场,再次恢复了客观性的权威。只不过这次恢复要比黑格尔更为彻底,建构了足以改变观念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回顾发生于19世纪初到40年代中期德国哲学的发展过程,目的是要揭示马克思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于黑格尔,而非康德和费希特。在那段时间,事实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共同形成了与主观性哲学相抗衡的一方。1978年以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哲学界为适应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需要,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的作用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旗帜”,由此而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主体性哲学”,对于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禁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再加上国外后现代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涌入,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观化的倾向。譬如,把主体性和实践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特征;强调主观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用偶然性和历史虚无主义代替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夸大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把马克思哲学康德化或费希特化等。针对这一思想状况,回顾上述时期德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质,纠正上述马克思哲学主观化的思潮,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主观性哲学的批判
众所周知,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思维、自我、自我意识等人的主观性因素被提高到主体的地位。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也从人之外转移到人之内,自我与本质实现了同一。这就是近代哲学所确立起来的主观性原则,或者称主体性原理。这一原则,在德国观念论传统中,特别是在康德及其后继者雅各比、费希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主观性被看成人类知识的最终依据和人的行为的归责根据。他们的哲学也因此被黑格尔称为“让美和真理表现为感情和情绪、爱和知性的主观性”哲学、“北方的原理”或者“新教的原理”[1]。
主观性哲学的出现为人类摆脱外部奴役、完成启蒙等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是近代哲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随着主观性地位被无限提升,自我从上帝或者实体那里被彻底剥离出来,与“绝对者(Absolutes)”之间发生了分离。人类因此而失去了绝对者的支撑,陷入了“理性自身的空虚(Nichtssein)”[2]。为了弥补这一空虚,一方面,人们试图让主观性取代过去上帝或者实体所拥有的地位,从主观性出发去完成自我与绝对者的重新统一。黑格尔把这种尝试称为“主观性的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ubjektivitt)”[3];另一方面,像康德哲学那样,它又让主观性停留于此岸世界,让绝对者安身于彼岸世界,从而使自我与绝对者无法融合。黑格尔曾这样描述“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悖论:“存在的独断论被改造成思维的独断论,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被改造成主观性的形而上学。……这样一来,作为自我中的物、实践理性的灵魂,就转化为主观的人格性和个别性的绝对性———但作为物的世界转化为现象的体系或者主观的情绪和可信的现实的体系———而理性的对象以及作为绝对的客观的绝对者转化为理性认识的绝对彼岸。”[4]如果彼岸世界对有限理性来说只能属于信仰领域的话,那么“主观性的形而上学”事实上又造成了知识与信仰的分离。本来,“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初衷是要将理性从中世纪神学中解放出来,使其从婢女上升为主人,但是将绝对者置于彼岸世界的做法,又等于使理性重新沦落为“信仰的婢女”。大约是在1800年前后,黑格尔意识到主观性哲学所存在的困境,试图通过主观性哲学的批判和客观性的重建来摆脱这一困境。
青年黑格尔最初是康德哲学的追随者,曾以康德的主观性原理批判过基督教。但是,在1801年到耶拿以后,在《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体系的差别》(1801,以下简称《差别》)《信仰和知识》(1802)《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自然法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证法学的关系》(1802~1803)等几篇论稿中,开始从对主观性的膜拜转向了对主观性的批判。《差别》一文的主题是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Identitt von Subjekt und Objekt)”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己所处的时代出现了“绝对者的现象与绝对者隔离开来”[5]的奇异状况。本来,“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者’的思想的历史。绝对者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6]而绝对者必须是“整体的真理”,其现象和本质必然是同一的,同一性才是绝对者的真理。但在主观性哲学盛行的“时代的教养(Bildung)”[7]下,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信仰和知识、自由与必然等,一句话主观和客观陷入了绝对的“分裂(Entzweiung)”之中。这种“分裂”不仅与哲学的目的本身相矛盾,反映在现实上,还带来了主观自由的泛滥,个体主观性对宗教、伦理秩序、世界历史等的破坏。因此,当下“哲学的需要”是重建被破坏了的绝对者,恢复“主观和客观的同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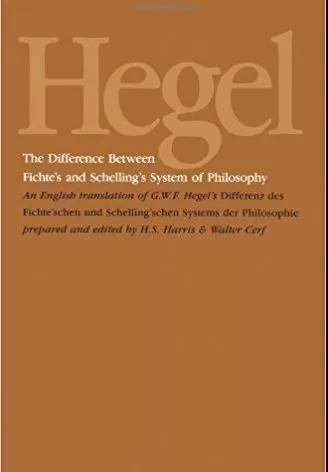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之所以陷入“分裂”之中,起因于康德哲学。在《信仰与知识》中,他分析了康德哲学的二元论问题。康德区分了现象界与物自体,提出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本身,这是由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知性(Verstand)”,一种是“理性(Vernunft)”。知性是对感觉经验整理和加工的能力;而理性作为人先天的认识能力,是指“认识无条件的事物的能力”[8]。如果说“知性”所处理的是经验世界的事物,而理性则要处理灵魂、世界和上帝等超验对象。知性虽然是科学知识的来源,但由于它依赖于人的感觉经验,以它来把握外部世界,会割裂与事物本身的联系。黑格尔批评道:“知性把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彻底分开,结果让客观的东西变成了完全无价值的东西,变成了无。这样,主观的美这一斗争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主观为抵御变为客观的必然性而努力维持自身。因此,美怎样在主观中成为实在,怎样将自己交给客观性,还有意识在什么地方将自己表现出来,成为客观性,去现象,在现象中生成,这些问题都被彻底省略掉了”[9]。
理性的本来目的则在于超越知性的限制,达到对事物本身的认识。理性的这一特点是符合哲学本身的目的的。但是,在康德那里,理性一旦要认识超验事物,非但不能把握到事物本身,反而会陷入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这一矛盾的出现本来是必然的和积极的,它可以推动人类认识进入事情本事。但可惜的是,康德在矛盾面前止步不前了,反而让理性退回到知性,把它只看成“在无限对立中的实践能力”或者“纯粹知性统一的能力”[10]。其结果,“理性除了提供简单化系统化经验所需的形式统一以外,没有别的,在这样的意义下,理性只是真理的规则,不是真理的工具。理性只提供知识的批判,而不能提供关于无限者的理论。”[11]也就是说,理性实际上被降低为知性。尽管康德并不承认经验知识本身就是真理,但无论是从他的知性概念还是从他的理性概念来看,他所承认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经验的存在、日常世界和现实”[12]。这与经验主义颇为相似,故后来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把他与经验主义者归为一类[13]。
前面说过,哲学的目的是要让自己进入主观性之外的物自体领域,去把握绝对者。但是,康德让哲学认识停留于经验层面,变成了单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或者对主观性形式的研究。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并没有完成哲学本身的任务。他的观念论只不过是“有限者的观念论(ein Idealismus des Endlichen)”[14];哲学必须通过从知性到理性的运动到达绝对者、无限者,因此是“绝对观念论(absoluter Idealismus)”。黑格尔本人也把自己的立场称作“绝对观念论”。当然,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对知性到理性的运动论述还不够成熟,直到《大逻辑》和《哲学全书》(《小逻辑》)才成熟起来。
康德以后,雅各比、费希特等人都试图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分离问题。在《差别》一文中,黑格尔主要分析了费希特的尝试。费希特延续了“康德哲学的精神”[15],从代表主观性的“自我=自我”出发来证明主观与客观或者“自我”与“非我”的同一性。费希特的“自我=自我”实际上是对笛卡尔命题“我思故我在”的展开,即从“我思”这一思维行为出发推导出了“我在”,其核心是将“我思”的自我反省活动换成了“行为(Handlung)”和“事实(Tat)”相统一的“事实行动(Tathandlung)”。在知识学的第二原理中,费希特通过“自我”的设定活动给出了“非我”这一客观性。但是,由于“非我”的被动本性,“自我”设定“非我”的活动就类似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行为,“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因此也变成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这样的因果关系。“自我”是因,“非我”是果。在因果关系下,“非我”没有独立性,它是“自我”为实现自身而被设定出来的客观性;“客观是一个绝对由自我规定之物,因而=自我。”[16]“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也只能是“纯粹的自我意识”中的同一性[17]。
对此,《黑格尔传》的作者罗森克兰茨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费希特哲学“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都没有把客观理解为是与主观相对立的、积极的、自立的东西,而只是把客观理解为否定性的限制。因此,它也就没有把绝对者理解为客观和主观的同一性”[18]。事实上,对“自我”与“非我”关系的因果式理解还将加剧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因为,正像神学中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作为原因的主观性作用越被强化,作为结果的客观性的被动性也就越被夸大,客观性因被彻底抽去了能动性、活动性而沦落为静止的死的自然。这样一来,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不再有任何相容的东西,两者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大。
既然“理论理性”遇到了困难,那么“实践理性”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实践理性部分,费希特试图让“自我”通过实践而把自己转变为“非我”,以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同一。但是,由于这一转变仍然是在“自我”与“非我”的因果关系下实现的,那么“非我”就不可能超出“纯粹意志”的辐射范围,它所实现的“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仍然是相对的,而非真正的自我与绝对者的融合。到头来,费希特还是不得不将“主观和客观的同一性”看成自我不断接近,但又无法到达绝对者的“应该”状态。“应该”就意味着在现实中主观性与客观性无法实现融合,两者处于对立之中。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这样总结这个推理:“费希特也仍然停滞在康德哲学的结论里,认为只有有限的东西才可认识,而无限便超出思维的范围。”[19]

总之,在《信仰与知识》一文中,黑格尔把康德、雅各比和费希特统称为“主观性的反省哲学”(该文的副标题) ,把他们的共同特点归纳为:“有限性的绝对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有限和无限、实在性和观念性、感性之物和超感性之物的绝对对立;还有真正实在的东西和绝对的东西存在于彼岸。”[20]先不论他把这三人归为一类是否合适,也不论这一归纳是否能被康德、雅各比和费希特的研究者们所认同,如果按照这三个特点,那么“反省哲学”的确不可能完成主观与客观的同一论证,“这些哲学与经验世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它们仍然停留在直接经验的领域”[21]。他们的方案之所以不成功,在黑格尔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给主观性以绝对的主动地位,给客观性以绝对的被动地位,通过这种因果关系来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同一。结果事与愿违,主观与客观的分离非但没有被消除,反而变得变本加厉。主观性成了自我与绝对者融合的最大障碍。
二、黑格尔的解决方案
既然问题出在客观性,那么能否让客观性也发挥积极作用,从客观性一侧去实现与主观性的同一呢?这显然是主观性哲学所忽略的思考方向。这一方向首先潜藏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在传统哲学中,实体或者自然往往代表着客观性,斯宾诺莎曾将实体视为自因,将一切都看作实体的自我展开过程。谢林比较早地发现了斯宾诺莎实体的意义。1800年以后,他与费希特论战过程中,出版了《先验的观念论体系》(1800)、《论自然哲学的真正概念》(1801)和《我的体系的阐述》(1801)等作品,尝试着从作为实体的自然一侧出发去完成绝对者与自我相融合的任务。
谢林的这一尝试,得到了黑格尔的赞同,事实上也成为黑格尔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问题的思想基础。在黑格尔看来,主观性哲学在解决“主观与客观同一性”问题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轻视了客观性。因此,就需要把客观性提高到与主观性并列的地位,让客观性也发挥与主观性同样的作用。黑格尔与谢林一样,不再把客观性(实体)仅仅看作单纯由主观性建立起来的僵死不动的被造物,而是把它看成一个类似于主观性那样的活的存在。费希特没有把“自我”单纯地理解为主观性,而把它理解为“主观与客观”是正确的,因为这等于让主观性包含客观性,为主观性向客观性过渡埋下了伏笔。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将客观性也看成“主观与客观”,让客观性本身中也包括主观性因素,从而为客观性向主观性过渡也埋下伏笔。黑格尔说道:“要使绝对的同一性成为整个体系的原理,主观与客观两者就必须都设定为主观=客观”,“在费希特的体系里,同一性只建立了一个主观的主观=客观。为了完善他的体系,需要给他补充一个客观的主观=客观”[22],只有这样,才能为完成主观与客观的同一开辟道路。
不仅如此,主观性与客观性两者的同一必须是在保持双方非同一性的基础上,通过矛盾运动所实现的对立统一,用黑格尔的话说,即“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同一性(die Identitt der Identitt und der Nichtidentitt)”[23]。只有这样的同一,才算是主观与客观的同一。只有在这种同一中,哲学才算实现了自我与绝对者的融合。在这一问题上,如果说黑格尔与谢林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黑格尔更强调主观与客观的分裂和对立对于到达绝对者的意义,强调绝对者必须是保持着差别或者非同一性的同一性;而谢林似乎对这一点认识不足,谢林更强调绝对者规定的无差别性、无矛盾性,谢林所说的同一性只是“同一性的同一性(Identitt der Identitt)”。
要想从绝对者一侧去实现与自我相融合的任务,在原理上就必须让代表客观性的实体运动起来,让它自己展现自身,去接近自我。而运动往往是主体的属性,那么让实体与主体结合起来就成了理论上的必然。如上所示,在耶拿前期黑格尔已经让客观性包含了主观性,其目的就是希望客观性也能像主体那样具有运动起来的含义。到了耶拿晚期,这一思想已经成熟,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他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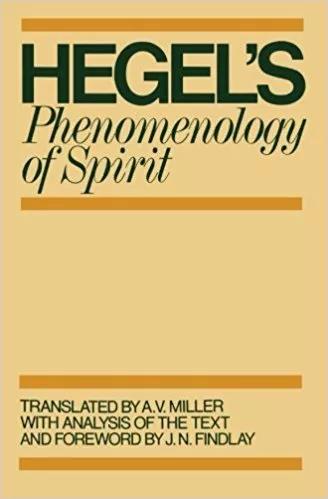
关于“实体即主体”命题,黑格尔这样写道:“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24]“活生生的实体是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就其真理而言是一个主体,或者换个同样的说法,这个存在就其真理而言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是一个自己设定自己的运动,或者说一个以自身为中介而转变为另一个东西的活动。”[25]这段话的含义有两层,其一,这段话反映了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对实体理解的差异。实体的本性固然在于与自身的同一,但在斯宾诺莎那里,这种同一是不变的,它无法产生出自我意识这样的差异。而黑格尔则把实体看作其自身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了实体异化为自我意识这样的差异环节。其二,虽然自我意识只有在实体中才能发现自己的普遍本质,但是另一方面,实体也只有通过自我意识这一中介才能认识自身,发展自身。实体与自我意识共同运动,最后达到绝对精神或者绝对知识。这就是黑格尔著名的“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原理。在这一原理中,自我意识作为最为典型的主体,它对于实体实现自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实体要从差别和对立中恢复自身,其力量主要来自于自我意识。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实体实现自身的必经之路。
总之,黑格尔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方案实际上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作为实体的精神只有通过主体这一中介,在自身内部设立起差别,然后再通过扬弃异化和差别,达到绝对的同一(“绝对精神”) ,这反映了耶拿早期以来从绝对者去接近自我的思路;另一方面,自我意识也要借承载实体运动的机会,经验“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知识”)等不同阶段,最终将自己提升为精神,这反映了从自我去接近绝对者思路。如果前者可称作“精神的现象”的话,那么后者就是“意识的经验”。正是通过这两个过程,黑格尔让哲学实现了绝对者与自我的融合,《精神现象学》本身也不外乎是这两条思路的结合。
诚然,黑格尔为纠正主观性哲学的错误,曾严厉地批判了“主观性的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主观性本身。因为,自我意识中所包含的活动性、主动性和目的性因素依然是哲学到达绝对者的关键环节。作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对黑格尔而言,主观性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被放弃的,这是他的一贯立场。早在《差别》一文中,黑格尔就把费希特那种从主观性出发的做法称为“先验哲学”;把谢林那种从客观性出发的做法称为“自然哲学”。他认为这两种哲学固然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都无法单独完成主观与客观相同一的使命,两者只有互相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自我与绝对者的融合。后来随着与谢林的决裂,到了耶拿晚期,他更积极地将自我意识引入“实体即主体”命题中来,以至于在整个《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自我意识向精神的运动占了大部分篇幅。从这一事实出发,很多黑格尔专家,譬如霍耐特等人就认为耶拿晚期黑格尔有一个向费希特接近的阶段,将耶拿晚期的思想规定为“意识哲学”[26]。但是,这种对主观性的认同并没有使黑格尔改变自己的客观观念论立场。作为一个事实,相对于康德和费希特,他更强调让绝对者去接近自我的方向,并承认主观性之外存在着可以认识的实体或者绝对者。在这点上,他的观点与主观性哲学有着实质性差别。
三、重建客观性的意义
从黑格尔的主观性批判和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同一性”问题的方案来看,黑格尔的哲学显然属于一种新哲学。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他曾将当时的哲学立场划分为三种:第一种为“把上帝理解为唯一的一个实体”,指以实体为核心的斯宾诺莎立场;第二种为“坚持着严格意义上的思维,坚持着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指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立场;第三种“即思维把实体的存在与自己合并,并把直接性或直观性活动理解为一种思维”,指实体与自我意识相统一的谢林的立场。黑格尔把自己划归为这第三种立场[27]。
那么,这第三种立场究竟指什么呢?我们知道,《精神现象学》中的黑格尔已经与谢林分道扬镳。早年的谢林为了超越康德哲学引入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将斯宾诺莎的实体一元论改造成自然哲学,并试图通过自然的自我生成来解决从自然中引出自由的问题。黑格尔虽然在耶拿早期追随谢林,但到了耶拿晚期,他意识到谢林的做法会遇到“夜间观牛,其色皆黑”的困难,于是就决定不再以斯宾诺莎的实体而以“自我展开的理念”为出发点。这一理念既不是实体,也不是自我意识,而是一种可以产生两者的客观理念。它通过自身的运动,产生出自然与自由、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对立,最后又通过对立统一,到达绝对者。这一客观理念,可以说就是黑格尔所理解的第三种立场。
这一客观理念,对于我们把握黑格尔的客观性规定是十分重要的。关于客观性,黑格尔曾在《小逻辑》的“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论述中,给出过自己的规定:“康德所谓思维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是主观的。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之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与此相反,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客观性一词实具有三个意义。第一为外在事物的意义,以示有别于只是主观的、意谓的或梦想的东西。第二为康德所确认的意义,指普遍性与必然性,以示有别于属于我们感觉的偶然、特殊和主观的东西。第三为刚才所提出的意义,客观性是指思想所把握的事情自身,以示有别于只是我们的思想,与事物的实质或事物的自身有区别的主观思想。”[28]从这一说明来看,黑格尔的客观性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康德的二元论。康德也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但它仍然是指人的思想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譬如统觉的先验统一性为人类思维所赐,存在于意识的范围内,属于主观性内部的客观性。而黑格尔的客观性则是指“对象性的本质”或者说“思想所把握的事情自身”,是外部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性质,是一个超越主观性的客观性。如果借用康德哲学的分法,它存在于“物自体”之中。

但是,黑格尔的客观性并不是像列宁等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独立于我们的感觉,又能被我们的感觉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即物质的属性。事实上,黑格尔和康德一样,对物质或者“外在事物”给予了很低的评价,认为它们是主观的、偶然的东西,没有超出感觉经验的范围。黑格尔所理解的客观性是存在于“外在事物”中的逻辑结构,这是只有思想或者理念才能给出的。而又由于思想或者理念不存在于我们的主观世界,而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世界,故可称作客观思想或者客观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谓的客观性并非是物质的客观属性,而是思想或者概念的客观属性。由于黑格尔让思想和理念成为“物自体”的本质,在坚持唯心主义立场上,黑格尔比康德还要彻底,所以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把黑格尔看成最大的唯心主义者。
但无论怎么说,这种客观观念论或者绝对观念论,毕竟承认了有高于自我意识的绝对的存在,这也就等于在主观性之外设定了一个能够限制自我意识的绝对者。这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有着特殊意义。19世纪初,德国观念论在通过主观性来完成启蒙任务之余,还出现了将主观性绝对化的思潮。这表现在个人的主观自由被说成唯一合理的,而外部的绝对物,譬如国家、宗教、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反倒成了值得怀疑的东西。其结果,就像我们在法国大革命中所看到的那样,国民主观自由的释放,非但没能实现主观自由与理性规律的统一,反而带来了自由泛滥的恐怖主义。黑格尔看到了主观性哲学的负面作用,从当时德国的思想状况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出发,试图通过重建客观性的权威来对主观化思潮予以纠正。这一努力贯彻了黑格尔的一生。在晚期的《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针对施雷格尔和弗里斯等人把真理和道德的根据都归结为主观因素的原则,称他们的“这些原则是把法的东西安置于主观目的和私见之上,安置在主观情感和私人信念之上的。从这些原则出发,其结果不仅使内心伦理和公正良心毁灭,使私人之间爱情和权利毁灭,而且使公共秩序和国家法律毁灭。”[29]同样,在《宗教哲学》中批评了施莱尔马赫的“感情神学”以及“被路德称为信仰的主观方面”的神学理论,称“把宗教置于单纯主观的方向———吾心即万物———已经毁灭了崇拜,并且像毁灭了由崇拜的主观心灵走向行动的过程0那样,也毁灭了意识走向一种客观知识的过程。”[30]
但是,黑格尔的意图和努力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黑格尔去世以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作出两方面事情,一方面攻击黑格尔的客观观念论,把他对客观性的偏重看作是其哲学的保守之处或者糟粕,把他的实体或者绝对精神概念看成对自我意识的压制。主张出于否定国家、宗教和法律等革命需要,必须革掉客观性或者实体的命,以便为自我意识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避免直接和黑格尔对决,将自己打扮成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传人,又采取了用主观性来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办法。于是,“实体即主体”或者“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原理,被鲍威尔解释成黑格尔主张“主观神学”的铁证,其哲学也被解释成费希特式的主观观念论。其结果,黑格尔好不容易开启的德国观念论传统的客观性转向,又被青年黑格尔派彻底扭转过来,德国哲学出现了向主观性的复辟。这次复辟要比费希特他们走得还远,实体被彻底视为主观性实现的障碍,整个外部世界都被视为主观性的产物,主观性哲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转向直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才被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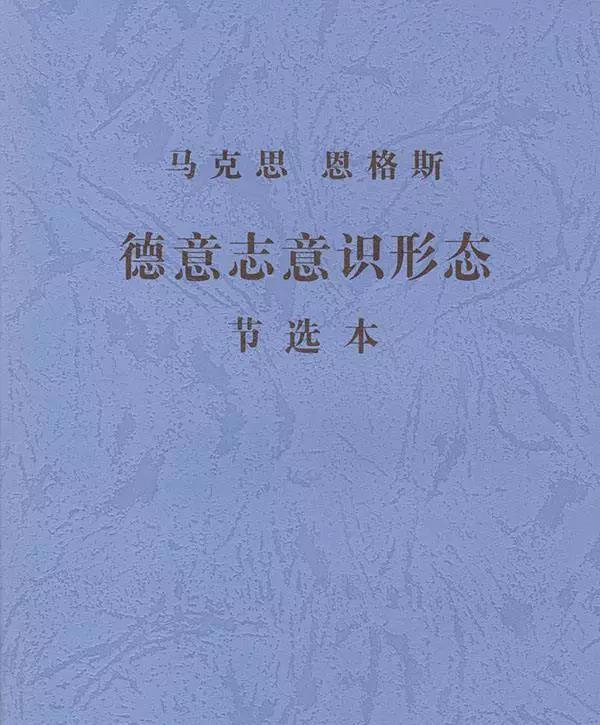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是双重的:第一,在“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很多时候对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与黑格尔不作区分,把他们都归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巴黎手稿”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马克思甚至指责黑格尔把实体即现实的人和世界都归结为自我意识。当然,从上面黑格尔对主观性哲学的批判来看,这一指责不够公正。但是,第二,马克思又认识到了黑格尔与鲍威尔之间的差别,认为黑格尔在现实性和客观性的认识上优于鲍威尔。马克思之所以采取这种双重态度,主要跟黑格尔本人的立场有关,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黑格尔出于对主观性哲学批判的需要,拒绝把实体归结为自我意识,在以思辨形式叙述的内部肯定了实体和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又把客观理念看作绝对者的本质,同时在实体运动中给自我意识以主导的地位,从而又为将实体归结为自我意识提供了方便。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存在的内部矛盾。鲍威尔试图通过以自我意识来解消实体的方式来克服这一矛盾,结果将黑格尔哲学彻底主观化了。马克思则显然不同意他的做法,认为这一矛盾的存在恰好表明黑格尔远高于同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写道:“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么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象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31]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如果要解决黑格尔体系的矛盾,其努力方向必须与鲍威尔的相反,应该去拯救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因素,更加彻底地恢复客观性权威,这与黑格尔在面对“主观性的形而上学”时所采取的态度基本一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应该是盟友关系,他们与康德的后继者费希特以及鲍威尔等人才是敌对关系。关于青年黑格尔派对主观性的复辟以及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过程较为详细的分析,尚需新的探讨。
注释:
[1][2][3][4][9][12][14][20][21]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Glauben und Wissen, oder die Reflexionsphilosophie der Subjectivitt, in der Vollstndigkeit ihrer Formen, als Kantische, Jacobische, und Fichtesche Philosophie, Gesammelte Werke, Bd.4, Felix Meiner Verlag, 1968, S.316, S.315, S.412, S.412, S.317, S.318, S.322, S.321, S.321.
()[5][7][10][15][16][17][22][23]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1801) , In: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Werke in zwanzig Bnden 2, Theorie Werkausgabe, Suhrkamp, 1970, S.20, S.20, S.11, S.9., S.68, S.57, S.94, S.96.参见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宋祖良、程志民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 1994,第9页;第9页;第2页;第1页;第46页;第37页;第66页;第68页。
[6][8][11][13][19][28]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2007,第10页;第126页;第141页;第116页;第151页;第120页。
[18]Karl Rosenkranz,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Leben,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69, S.149.
[24][25][2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先刚译,人民出版社, 2013,第11页;第12页;第11页。
[26]参见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第38页。
[2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61,第8页。
[30]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Religions-Philosophie,
In:Vorlesungsmanuskripte I (1816-1831) , Gesammelte Werke, Bd.17,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87, S.38.参见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手稿I (1816~1831)》,《黑格尔全集》第17卷,梁志学、李理译,商务印书馆, 2012,第6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9,第358、359页。

